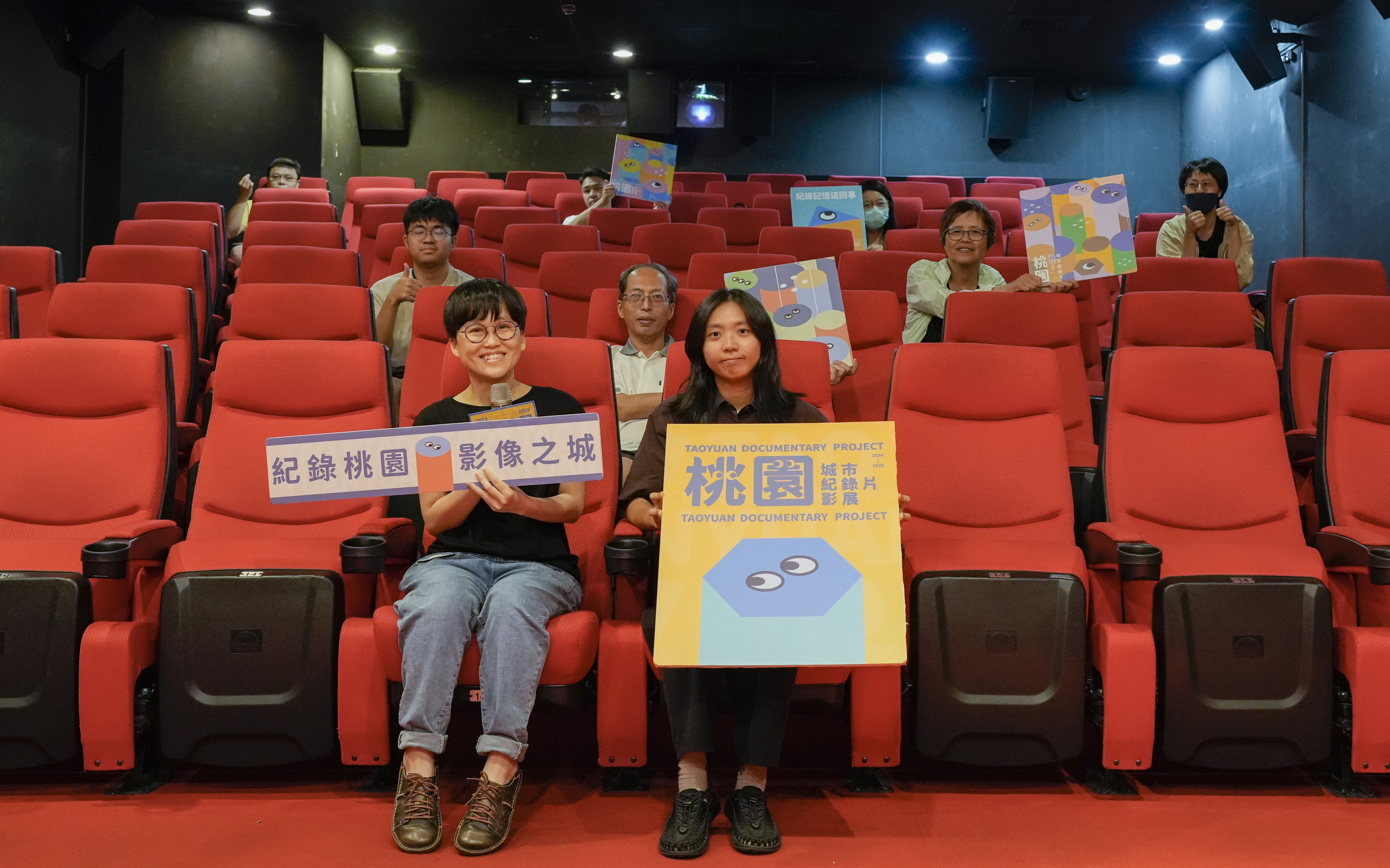《蜻蜓飛過的歲月》映後座談
▋時間:2025/9/27 (六) 18:30
▋地點:中壢光影電影館
▋主持人:辛佩宜
▋映後與談人:葉家辰 導演
※ 本場次與「TIDF巡迴展」合作放映
▶ 主持人:邀請家辰擔任這部片的與談人,家辰的年紀與《蜻蜓飛過的歲月》導演洪多藝相近,成長於同一個世代,這個世代的價值觀、升學主義,可以有台灣跟韓國的對照。另外,也因為家辰許多作品也也就是紀錄年輕世代的自我認同探索、對於生命的困惑等等。想請家辰先聊聊你對這部影片的整體感受。
▶ 家辰 導演:這是我第二次看這部片,我第一次在影展觀影,導演有出席映後。這次重看了一次,我覺得比之前又更喜歡這部片子,原因有很多,這部片製作的歷程很長,從2014年開始拍,直到2021年成片,這段過程中他在每個人生重要事件發生的時刻,他會一直問自己「為什麼我要拍這部片?這部片的意義是什麼?」這整個攤開梳理自己的過程很打動人心。導演在片中有提到,2014年拿起攝影機時,原本是想控訴升學體制,身為升學體制內的人,去拍攝升學體制的荒謬,但是這部紀錄片的意義,隨著他進入大學後、失去朋友之後,他發現這份痛苦一直沒有消失。這件事其實回歸到紀錄片的本質,回到最小的地方來看,過去的那些影像(記錄了朋友的身影),時隔多年回看過去的記憶而產生力量,這件事情很讓我觸動。
___________
▶ 主持人:家辰同樣是影像創作者,拍攝過程中同樣會邊拍邊尋找答案。《蜻蜓飛過的歲月》裡一直出現蜻蜓、蝴蝶的意象,整個社會環境一直灌輸我們「好好唸書上大學,一切就會不一樣」,我們就會破蛹而出變成美麗的蝴蝶。但我自己看的時候,都覺得我現在也還是那隻在水裡掙扎的蜻蜓,不知道家辰、在座的觀眾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下長大?
我們可以看到導演上大學後,其實陷入另一種人生迷惘的狀態,也有上街頭參與社會運動。想問問家辰,你上大學後,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尋找自我價值?
▶ 家辰 導演:這也是這部片另一個很打動我的部分。我高中時其實不清楚自己喜歡什麼,大學考上了社會系,在一個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的階段,不得不進入升學體制的遊戲,進大學後,接觸很多不同事物,才發覺自己喜歡電影。街頭運動也讓我很有感,大學時期經歷太陽花運動,跟著大家去立法院,也去了樂生療養院。我覺得人生好像在那個階段開始有了選擇權,當有機會決定自己要什麼的時候,那個當下其實是非常茫然的,什麼都接觸看看,但還沒收攏成自己的樣子。
___________
▶ 主持人:影片中看到導演最初開始紀錄同學,後來因為重考,拍自己重考、拍朋友上大學,接著上了大學有更多的困惑,因此在影片敘事上,他開始轉向自我、攝影機也轉向自己,有更多的自我揭露。觀眾看見更多他的內在生命狀態,家辰怎麼看待導演這樣的敘事編排?
▶ 家辰 導演:紀錄片歷時很長,很多舉起攝影機的瞬間,會因為3年、5年之後,自己的狀態改變了,片子的狀態也跟著改變。我覺得洪多藝導演的狀態正是這樣,創作很多時候都是反應創作者自己的生命力歷程,這個轉向是非常真實的。而我自己也經歷了很多次這樣的轉向,原本以為想拍A,但是拍一拍發現,我在這件事情或這個人身上看見自己,發現我真正想講的是另一個更深的事情。洪多藝導演經歷這麼多年,做了一個很好的梳理,最後呈現他在那個階段得到的答案。
▶ 主持人:也因為片子拍了這麼多年,才有辦法處理很深層的面向。
▶ 家辰 導演:對,尤其把自己放進片子裡的紀錄片,距離很難拿捏,靠得太近會被捲進片子裡,沒有辦法跳脫出來看,那種「掙扎、放一下,再繼續剪」的過程是很可貴的。
___________
▶ 觀眾:剛開始看的時候,前面處理瑣碎的日常,但他們長大之後回看,很意想不到。想要問片名的部分,中文《蜻蜓飛過的歲月》和英文片名“Saving a Dragonfly”,意思蠻不同。中文可能有點像用蜻蜓比喻自己,英文片名像是希望有人能去拯救蜻蜓時代的自己。
▶ 家辰 導演:我自己取片名的時候,很喜歡英文、中文有不同的意思,會出現有趣的解讀空間。《蜻蜓飛過的歲月》這樣的片名呈現了事情過後雲淡風輕的感覺,多年之後重訪高中同學,大家其實已經記不太清楚了,但是那種痛苦還是很真實。
___________
▶ 觀眾:想請家辰分享當時參加導演映後,導演分享了什麼?另外也想問問家辰,你近期的紀錄片作品《弄青春》,被攝者是高中生,你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和態度和他們相處?
▶ 家辰 導演:我可以分享導演映後我印相深刻的部分,洪多藝導演一開始拍的時候,很明確想用紀錄片批判升學體制,但是他並沒有那麼有意識的要完成一部電影,當時只是每天大量大量的拍,2014年那時,每天每天都有幾10G的檔案,非常大量的素材,2016年上大學開始慢慢整理。起初整理素材時,從同學之間好笑的事情著手,一直到2021年片子剪完,過程中,他的生命也正發生很多重要的事件,促使他做剪接上的選擇、敘事核心的轉換。
至於《弄青春》,我的被攝者當時是高三要升大學,也處於升學的迷惘階段,他有自己的夢想追求。我在他身上回想我自己,高中這個階段特別會嚮往未來的事情,那種嚮往的感受很珍貴。到了一定年紀之後,就會知道每個生命階段,都還是有很多的問題、很多痛苦在發生。
___________
▶ 觀眾: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洪導演在車子裡和父母聊天,導演的媽媽哭著說:「其實大學沒什麼重要」這句話,我覺得是父母對孩子的回答。我身邊也有一些朋友在念高中,正在面對這些事情,會很希望台灣父母有機會接觸這類型的影片,了解孩子正在面對什麼,可以怎麼和孩子相處等等。
▶ 主持人:整支影片大人的篇幅不多,我們容易在這樣的場景想像,導演可能會想控訴體制裡的老師或家長,但導演處理的非常淡。
▶ 家辰 導演:那個控訴是觀眾看完後自己反思的部分,他就是呈現出自己面對這些事情時真實的情感,我還蠻喜歡這種純粹處理的選擇。
___________
▶ 主持人:很多紀錄片創作者,都是邊拍攝邊尋找自己生命真實的狀態,面對自己的困惑,嘗試找到一些答案,想問問家辰創作與你自己的關係是什麼?
▶ 家辰 導演:電影就是有這樣的力量,不論是看電影的觀眾或拍電影的人。
我自己的經驗,就是覺得「電影在很多時刻支持著我」。20歲的時候決定想拍電影,會有這個想法出現是因為我的人生遇到很大的衝擊事件。我的第一部紀錄片之所以會出現,是因為進了電影產業之後很痛苦,覺得自己適應不良、不夠社會化......,一度覺得要放棄電影了,就在那時刻,第一次拿起攝影機自己來拍,才有辦法堅持到現在。電影在很多時候,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存在。但是我和電影的關係?我還沒有答案。但現階段的我知道,我會繼續拍下去,也會繼續找答案。
▶ 主持人:電影很像創作者的鏡子,可以在裡面看到很多自己的投射和映照。